来怀柔过端午:到汤河口看龙舟赛
来怀柔过端午:到汤河口看龙舟赛
来怀柔过端午:到汤河口看龙舟赛 北京120调度(diàodù)指挥中心。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刚成为医学生(yīxuéshēng)那会儿,这些年轻人没想过毕业之后(zhīhòu)“去120接电话”。
他们接的每一通电话(tōngdiànhuà)都很紧急:孩子呛奶窒息(zhìxī),老人失去意识昏迷,产妇在家临产,危重病人需要转院,还有车祸、火情,以及一座常住人口超过2100万的超大城市里(lǐ)的各种突发状况。
在北京,平均(píngjūn)每30秒就有一辆120救护车接到(jiēdào)这里的(de)指令,驶向救人的现场。三十多年来,北京急救中心调度大厅的调度岗(gǎng)席位从3个增至30多个,急救调度员的声音此起彼伏——“您好,120,需要救护车吗?”
他们的(de)实际角色是“调度医生”,脑子里装着整个北京市的地图和400多个急救站点的位置。在(zài)派出的急救车组到达之前,他们会(huì)通过电话远程指导家属或好心的陌生人(mòshēngrén),给孩子解除气道异物梗阻、给产妇接生、给心搏骤停的患者做心肺复苏。
一个临床医学专业(zhuānyè)的120调度医生,工作(gōngzuò)了二十几年,没给病人开过一张处方,却“救活过许多人”。
在危重紧急的现场,两辆(liǎngliàng)摩托开着(kāizhe)警笛为急救车开道,医院(yīyuàn)早已建好绿色通道等待。少有人知道(zhīdào),120的调度医生人虽不在现场,却可以协调119、110、122“警医联动”,一键启动联合救援,共同完成挽救生命的艰巨任务。
从120电话接通的那一刻起,一场急救(jíjiù)接力就(jiù)开始了。毫无疑问,调度医生们手握着的是生命线上的急救“第一棒”。
北京120调度(diàodù)指挥中心。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刚成为医学生(yīxuéshēng)那会儿,这些年轻人没想过毕业之后(zhīhòu)“去120接电话”。
他们接的每一通电话(tōngdiànhuà)都很紧急:孩子呛奶窒息(zhìxī),老人失去意识昏迷,产妇在家临产,危重病人需要转院,还有车祸、火情,以及一座常住人口超过2100万的超大城市里(lǐ)的各种突发状况。
在北京,平均(píngjūn)每30秒就有一辆120救护车接到(jiēdào)这里的(de)指令,驶向救人的现场。三十多年来,北京急救中心调度大厅的调度岗(gǎng)席位从3个增至30多个,急救调度员的声音此起彼伏——“您好,120,需要救护车吗?”
他们的(de)实际角色是“调度医生”,脑子里装着整个北京市的地图和400多个急救站点的位置。在(zài)派出的急救车组到达之前,他们会(huì)通过电话远程指导家属或好心的陌生人(mòshēngrén),给孩子解除气道异物梗阻、给产妇接生、给心搏骤停的患者做心肺复苏。
一个临床医学专业(zhuānyè)的120调度医生,工作(gōngzuò)了二十几年,没给病人开过一张处方,却“救活过许多人”。
在危重紧急的现场,两辆(liǎngliàng)摩托开着(kāizhe)警笛为急救车开道,医院(yīyuàn)早已建好绿色通道等待。少有人知道(zhīdào),120的调度医生人虽不在现场,却可以协调119、110、122“警医联动”,一键启动联合救援,共同完成挽救生命的艰巨任务。
从120电话接通的那一刻起,一场急救(jíjiù)接力就(jiù)开始了。毫无疑问,调度医生们手握着的是生命线上的急救“第一棒”。
 院前医疗救治转运(zhuǎnyùn)危重症患者。
“从两分钟缩短到(dào)90秒,然后是1分钟,有时仅需50秒”
5月一个雨天的上午10点,北京(běijīng)有433辆救护车正在执行任务。
在调度员姜宇婷面前的电脑屏幕(diànnǎopíngmù)上,一些被标记为红色的救护车图标代表正在执行任务(rènwù)中,此时穿梭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救护车有21辆车是她派出去(qù)的。
工作(gōngzuò)进入第十个年头,她不会“在上班的前一天就开始紧张了”,但也没办法放松下来。“这是一个没办法松弛的工作,需要精神高度集中,绝不能(juébùnéng)出错(chūcuò)。”姜宇婷补充说,“出错就可能是人命”。
和(hé)大部分急救调度员一样,来120上班前,她对(duì)这项工作一无所知,而现在“对这份职责和使命却有了深刻的体会”。
孙婧学的是临床医学(línchuángyīxué),从事急救调度工作后她发现,“每天都有一百多种焦虑从电话那端传来”。工作快(kuài)20年,只要电话那头的语速一快,她的精神马上(mǎshàng)就会“跟着‘跑’起来”。
职业经验(jīngyàn)让她学会保持冷静并让对方“淡定降速”,在她的引导下(xià)完成有效(yǒuxiào)信息采集。“我必须专业,问出重点,才能迅速调派救护车开展救治。”孙婧说。
上岗的前(qián)几个月,新来的年轻人打字(dǎzì)要练,地图要背,说话都要学,这是“最基础的基本功”。
为了更快地背下那些环路和桥,姜宇婷按老调度的(de)经验(jīngyàn),歇班的日子就坐(zuò)公交车在北京环路上一圈圈地转。考核时,他们要在部分空白的地图上,填上路名和桥名。
穿着胸前和后背处印着蓝色“北京120急救”的白色工作服,姜宇婷戴着麦克风和听筒在同一侧的耳机,和师傅姚楠接入同一台电话,她(tā)只能听。这部电话会(diànhuàhuì)一点点(yìdiǎndiǎn)移交给她。
除了吃饭和(hé)去厕所,耳机不能摘,保证(bǎozhèng)电话进来时立即能接听。科里的规定是“10秒内接听电话”。
两通电话的间隙,偶尔(ǒuěr)有医生站起来做做扩胸运动,或者扭扭(niǔniǔ)腰。他们每班12个小时,久坐可能让他们的腰肌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。调度大厅外的墙壁(qiángbì)上贴着一张《预防腰椎间盘突出症需要(xūyào)注意哪些事项》,每名调度医生上下班等电梯时都能“温习一遍”。
姚楠的左耳被压在听筒下25年,除了听对方说话,还要识别背景音(yīn)——急促的呼吸声、喘鸣声或是异样的鼾声。她现在偶尔觉得听得不够清楚,常换到另一只“非惯用(guànyòng)耳”。但(dàn)没多久又换回来(huànhuílái),她嫌“另一只耳朵业务不够熟练”。
姚楠2001年入(niánrù)职,那时移动互联网刚萌芽,乔布斯的(de)第一代苹果手机要在6年后出现,中国的3G网络建设还要再晚一年启动。
和她同批(tóngpī)的调度医生入(rù)职时,电脑还没装完。他们背地图,背站点电话,学习五笔输入法,人手(rénshǒu)一本科里调度医生们自己编写的《医学指南》,在遇到突发情况时给出准确的医学指导。
如今,北京(běijīng)急救中心自主研发了更贴合(tiēhé)国情的高级调度在线生命支持系统ADLS——在调度席位的电脑里,每当他们输入病人的情况,就可以得到分步骤的医学指导,调度员可以依此对病人进行(jìnxíng)快速规范(guīfàn)的医学指导。
120调度系统(xìtǒng)也经历了好几代的升级改造。每个调度员面前有3块电脑屏幕:左边(zuǒbiān)是(shì)地图,中间是登记信息的受理屏,右边是车辆(chēliàng)信息。今年年初,他们接入了语音呼叫系统,只要求助者说清楚了姓名、地址和病情,他们点个按钮,待命的救护车就会接到出发指令。
系统还在持续优化。“我们主任老说(shuō),你(nǐ)是调度,有没有思考过如何让急救事业更往前发展一步?”孙婧笑着说,“好‘卷’是不是?”
每个月,他们都会统计这个月科里和每名调度员(diàodùyuán)派车的平均秒数。在技术和算法的支撑下,过去几年,派车时间从两分钟(liǎngfēnzhōng)缩短到(dào)90秒,然后是1分钟,有时仅需50秒。
50秒内,他们(tāmen)要做的事情太多了。
院前医疗救治转运(zhuǎnyùn)危重症患者。
“从两分钟缩短到(dào)90秒,然后是1分钟,有时仅需50秒”
5月一个雨天的上午10点,北京(běijīng)有433辆救护车正在执行任务。
在调度员姜宇婷面前的电脑屏幕(diànnǎopíngmù)上,一些被标记为红色的救护车图标代表正在执行任务(rènwù)中,此时穿梭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救护车有21辆车是她派出去(qù)的。
工作(gōngzuò)进入第十个年头,她不会“在上班的前一天就开始紧张了”,但也没办法放松下来。“这是一个没办法松弛的工作,需要精神高度集中,绝不能(juébùnéng)出错(chūcuò)。”姜宇婷补充说,“出错就可能是人命”。
和(hé)大部分急救调度员一样,来120上班前,她对(duì)这项工作一无所知,而现在“对这份职责和使命却有了深刻的体会”。
孙婧学的是临床医学(línchuángyīxué),从事急救调度工作后她发现,“每天都有一百多种焦虑从电话那端传来”。工作快(kuài)20年,只要电话那头的语速一快,她的精神马上(mǎshàng)就会“跟着‘跑’起来”。
职业经验(jīngyàn)让她学会保持冷静并让对方“淡定降速”,在她的引导下(xià)完成有效(yǒuxiào)信息采集。“我必须专业,问出重点,才能迅速调派救护车开展救治。”孙婧说。
上岗的前(qián)几个月,新来的年轻人打字(dǎzì)要练,地图要背,说话都要学,这是“最基础的基本功”。
为了更快地背下那些环路和桥,姜宇婷按老调度的(de)经验(jīngyàn),歇班的日子就坐(zuò)公交车在北京环路上一圈圈地转。考核时,他们要在部分空白的地图上,填上路名和桥名。
穿着胸前和后背处印着蓝色“北京120急救”的白色工作服,姜宇婷戴着麦克风和听筒在同一侧的耳机,和师傅姚楠接入同一台电话,她(tā)只能听。这部电话会(diànhuàhuì)一点点(yìdiǎndiǎn)移交给她。
除了吃饭和(hé)去厕所,耳机不能摘,保证(bǎozhèng)电话进来时立即能接听。科里的规定是“10秒内接听电话”。
两通电话的间隙,偶尔(ǒuěr)有医生站起来做做扩胸运动,或者扭扭(niǔniǔ)腰。他们每班12个小时,久坐可能让他们的腰肌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。调度大厅外的墙壁(qiángbì)上贴着一张《预防腰椎间盘突出症需要(xūyào)注意哪些事项》,每名调度医生上下班等电梯时都能“温习一遍”。
姚楠的左耳被压在听筒下25年,除了听对方说话,还要识别背景音(yīn)——急促的呼吸声、喘鸣声或是异样的鼾声。她现在偶尔觉得听得不够清楚,常换到另一只“非惯用(guànyòng)耳”。但(dàn)没多久又换回来(huànhuílái),她嫌“另一只耳朵业务不够熟练”。
姚楠2001年入(niánrù)职,那时移动互联网刚萌芽,乔布斯的(de)第一代苹果手机要在6年后出现,中国的3G网络建设还要再晚一年启动。
和她同批(tóngpī)的调度医生入(rù)职时,电脑还没装完。他们背地图,背站点电话,学习五笔输入法,人手(rénshǒu)一本科里调度医生们自己编写的《医学指南》,在遇到突发情况时给出准确的医学指导。
如今,北京(běijīng)急救中心自主研发了更贴合(tiēhé)国情的高级调度在线生命支持系统ADLS——在调度席位的电脑里,每当他们输入病人的情况,就可以得到分步骤的医学指导,调度员可以依此对病人进行(jìnxíng)快速规范(guīfàn)的医学指导。
120调度系统(xìtǒng)也经历了好几代的升级改造。每个调度员面前有3块电脑屏幕:左边(zuǒbiān)是(shì)地图,中间是登记信息的受理屏,右边是车辆(chēliàng)信息。今年年初,他们接入了语音呼叫系统,只要求助者说清楚了姓名、地址和病情,他们点个按钮,待命的救护车就会接到出发指令。
系统还在持续优化。“我们主任老说(shuō),你(nǐ)是调度,有没有思考过如何让急救事业更往前发展一步?”孙婧笑着说,“好‘卷’是不是?”
每个月,他们都会统计这个月科里和每名调度员(diàodùyuán)派车的平均秒数。在技术和算法的支撑下,过去几年,派车时间从两分钟(liǎngfēnzhōng)缩短到(dào)90秒,然后是1分钟,有时仅需50秒。
50秒内,他们(tāmen)要做的事情太多了。
 陈敏瑞(左一)和孙婧(右一)防汛应急(yìngjí)期间调度指挥。
调度医生(yīshēng)心里准备的若干个问题就像“肌肉记忆”
120急救没有(méiyǒu)“淡旺季”之分。
春天,过敏引起(yǐnqǐ)的哮喘患者多;夏天,热射病的发病(fābìng)人数上升(shàngshēng);城市煤改气前,一到冬天,总有一氧化碳中毒的。换季时,中老年容易突发心脑血管疾病。赶上节假日、雨雪天气,摔伤(shuāishāng)的、车祸的120呼叫量有所增多。
技术和算法让系统可以协助(xiézhù)派车。10年前他们按行政区域派车,2015年,北京市成为全国唯一实现(shíxiàn)统一指挥、一级调度的城市,无论呼救(hūjiù)者身处区域内何处拨打(bōdǎ)120,都会按照卫星定位就近调派救护车辆。
系统有时没有人聪明。120调度员就像急救网络的“神经中枢”,“精准统筹和动态调派急救力量”。救护车的配置和随车医生的资质与能力(nénglì)(nénglì)都(dōu)有统一要求,但还是会有呼吸机(hūxījī)、微量泵等“选配”器材的差别,医生的救治能力和经验值也不相同,这就需要(xūyào)调度员针对不同急危重程度的情况,人工指派相应急救车组。
“调度员(diàodùyuán)发出的派车(chē)指令就是院前急救人员的命令。”陈敏瑞觉得,对于调度员,“果断非常重要”。
120调度工作有着极为严格的质控要求,他们接听的每一通电话都可能接受复盘检查。通话录音会被多方反复(fǎnfù)审听,逻辑是否闭环,任务是否调派准确。甚至是,每一句话的语音语调是否合适——要照顾(zhàogù)求助者的情绪,调度医生(yīshēng)有很多“不能说(shuō)的话”,比如“打断一下”“说清楚点,你说不清楚能不能换个人(gèrén)说”。
一次车祸,公交车上七八个人受伤,陈敏瑞在(zài)第一时间先派出4辆救护车——“问清现场伤员情况,几个人躺(tǎng)着不能动,几个人可以坐着,初步判断出伤情(shāngqíng)的严重程度,明确派车数量。”她解释,根据现场情况,调度员按照(ànzhào)工作预案随时增援,会动态调整急救力量。
某次紧急任务,陈敏瑞派出几十辆救护车(jiùhùchē)。几名调度(diàodù)员组成调度专席——每辆车都要盯,接几个人,伤情(shāngqíng)是(shì)什么样的,准备送哪个医院,需要与哪些医院提前建立绿色通道等。同时,他们还要向车组及时通报路况。
突发事件(tūfāshìjiàn)的数据(shùjù)要时时统计更新,有多少人受伤,派出多少车辆,送去了哪些医院……调度员必须能准确地回答出来。
孙婧回忆,那次突发事件延续到了她下班时间,交接好工作后,她也不敢把手机调到静音,始终保持待命状态。因为家离单位近,她是工作预案里应急(yìngjí)队伍的“第一(dìyī)梯队”。她知道不一定(yídìng)会叫她,但她“做好了随时(suíshí)上班的准备”。
经验让她预判了情况(qíngkuàng)的复杂性。她是经历(jīnglì)过好几场火灾救援的调度员(diàodùyuán)。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,她听到“800兆”对讲机里119的直接呼叫,拿起手台之前“脑瓜子就嗡嗡的”。
一场大风造成了平房(píngfáng)起火,她的标准问题是:平房是联排吗?都有人(yǒurén)住吗?火还在烧吗?早些年,“回”型楼里(lóulǐ)的群租房着火,大火转着圈地烧。她“要对事情(shìqíng)有预判,会演变成什么情况,就一定要派足量的车”。
交通事故现场比较复杂,现场多人(duōrén)打电话进来,每名调度医生的屏幕上(shàng)都会显示此刻用车需求的位置。他们在调度大厅里会互通信息,组长要(yào)综合判断处理。
同样是客车发生事故,情况也不一样:和什么相撞?满载还是空载(kōngzài)?几个人受伤?有没有人员被困?撞击之后车辆有没有起火……调度医生心里准备的若干个问题就像“肌肉记忆”,要在第一通电话(diànhuà)(tōngdiànhuà)时“一把问清”,因为后续电话可能很难再接通(jiētōng)了。
“一把问清(wènqīng)”考察了他们的能力。大型商场或者多路换乘的地铁站,孙婧会在第一时间(shíjiān)问清楚,哪个入口离现场最近(zuìjìn),直梯在哪里——医生的急救包重10公斤,担架床需要直梯。她(tā)必须为车组确认找到病人的最快路线。
即便救护车到达现场了,他们的(de)工作还没完。遇到危重紧急的情况(qíngkuàng),有时需要110警察配合(pèihé),需要联动122交通部门(jiāotōngbùmén)在设定的路上为救护车清路,需要与附近接治医院提前建立绿色通道,环环相扣,都需要调度医生协调处理。
组长(zǔzhǎng)席上放着“四台联动”——110、120、119、122之间建立了(le)联动机制。调度医生可以用“800兆”对讲机直接呼叫,开启三方通话(tōnghuà)。
有家长在商场里(lǐ)拨打120,孩子(háizi)的(de)(de)3根手指被意外碾断。接电话的几秒钟,陈敏瑞想了“特别多关于孩子今后的工作和生活(的场景)”。“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就近派车,建立绿色通道,缩短(suōduǎn)孩子就诊时间。”她不忘嘱咐家长“断指一定要保存好,交给急救医生,这是再植的关键”。
“你有没有提前为(wèi)这些人再多做一步?”孙婧说(shuō),“我们的自我要求就是,不允许救援耽误在我身上。”
陈敏瑞(左一)和孙婧(右一)防汛应急(yìngjí)期间调度指挥。
调度医生(yīshēng)心里准备的若干个问题就像“肌肉记忆”
120急救没有(méiyǒu)“淡旺季”之分。
春天,过敏引起(yǐnqǐ)的哮喘患者多;夏天,热射病的发病(fābìng)人数上升(shàngshēng);城市煤改气前,一到冬天,总有一氧化碳中毒的。换季时,中老年容易突发心脑血管疾病。赶上节假日、雨雪天气,摔伤(shuāishāng)的、车祸的120呼叫量有所增多。
技术和算法让系统可以协助(xiézhù)派车。10年前他们按行政区域派车,2015年,北京市成为全国唯一实现(shíxiàn)统一指挥、一级调度的城市,无论呼救(hūjiù)者身处区域内何处拨打(bōdǎ)120,都会按照卫星定位就近调派救护车辆。
系统有时没有人聪明。120调度员就像急救网络的“神经中枢”,“精准统筹和动态调派急救力量”。救护车的配置和随车医生的资质与能力(nénglì)(nénglì)都(dōu)有统一要求,但还是会有呼吸机(hūxījī)、微量泵等“选配”器材的差别,医生的救治能力和经验值也不相同,这就需要(xūyào)调度员针对不同急危重程度的情况,人工指派相应急救车组。
“调度员(diàodùyuán)发出的派车(chē)指令就是院前急救人员的命令。”陈敏瑞觉得,对于调度员,“果断非常重要”。
120调度工作有着极为严格的质控要求,他们接听的每一通电话都可能接受复盘检查。通话录音会被多方反复(fǎnfù)审听,逻辑是否闭环,任务是否调派准确。甚至是,每一句话的语音语调是否合适——要照顾(zhàogù)求助者的情绪,调度医生(yīshēng)有很多“不能说(shuō)的话”,比如“打断一下”“说清楚点,你说不清楚能不能换个人(gèrén)说”。
一次车祸,公交车上七八个人受伤,陈敏瑞在(zài)第一时间先派出4辆救护车——“问清现场伤员情况,几个人躺(tǎng)着不能动,几个人可以坐着,初步判断出伤情(shāngqíng)的严重程度,明确派车数量。”她解释,根据现场情况,调度员按照(ànzhào)工作预案随时增援,会动态调整急救力量。
某次紧急任务,陈敏瑞派出几十辆救护车(jiùhùchē)。几名调度(diàodù)员组成调度专席——每辆车都要盯,接几个人,伤情(shāngqíng)是(shì)什么样的,准备送哪个医院,需要与哪些医院提前建立绿色通道等。同时,他们还要向车组及时通报路况。
突发事件(tūfāshìjiàn)的数据(shùjù)要时时统计更新,有多少人受伤,派出多少车辆,送去了哪些医院……调度员必须能准确地回答出来。
孙婧回忆,那次突发事件延续到了她下班时间,交接好工作后,她也不敢把手机调到静音,始终保持待命状态。因为家离单位近,她是工作预案里应急(yìngjí)队伍的“第一(dìyī)梯队”。她知道不一定(yídìng)会叫她,但她“做好了随时(suíshí)上班的准备”。
经验让她预判了情况(qíngkuàng)的复杂性。她是经历(jīnglì)过好几场火灾救援的调度员(diàodùyuán)。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,她听到“800兆”对讲机里119的直接呼叫,拿起手台之前“脑瓜子就嗡嗡的”。
一场大风造成了平房(píngfáng)起火,她的标准问题是:平房是联排吗?都有人(yǒurén)住吗?火还在烧吗?早些年,“回”型楼里(lóulǐ)的群租房着火,大火转着圈地烧。她“要对事情(shìqíng)有预判,会演变成什么情况,就一定要派足量的车”。
交通事故现场比较复杂,现场多人(duōrén)打电话进来,每名调度医生的屏幕上(shàng)都会显示此刻用车需求的位置。他们在调度大厅里会互通信息,组长要(yào)综合判断处理。
同样是客车发生事故,情况也不一样:和什么相撞?满载还是空载(kōngzài)?几个人受伤?有没有人员被困?撞击之后车辆有没有起火……调度医生心里准备的若干个问题就像“肌肉记忆”,要在第一通电话(diànhuà)(tōngdiànhuà)时“一把问清”,因为后续电话可能很难再接通(jiētōng)了。
“一把问清(wènqīng)”考察了他们的能力。大型商场或者多路换乘的地铁站,孙婧会在第一时间(shíjiān)问清楚,哪个入口离现场最近(zuìjìn),直梯在哪里——医生的急救包重10公斤,担架床需要直梯。她(tā)必须为车组确认找到病人的最快路线。
即便救护车到达现场了,他们的(de)工作还没完。遇到危重紧急的情况(qíngkuàng),有时需要110警察配合(pèihé),需要联动122交通部门(jiāotōngbùmén)在设定的路上为救护车清路,需要与附近接治医院提前建立绿色通道,环环相扣,都需要调度医生协调处理。
组长(zǔzhǎng)席上放着“四台联动”——110、120、119、122之间建立了(le)联动机制。调度医生可以用“800兆”对讲机直接呼叫,开启三方通话(tōnghuà)。
有家长在商场里(lǐ)拨打120,孩子(háizi)的(de)(de)3根手指被意外碾断。接电话的几秒钟,陈敏瑞想了“特别多关于孩子今后的工作和生活(的场景)”。“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就近派车,建立绿色通道,缩短(suōduǎn)孩子就诊时间。”她不忘嘱咐家长“断指一定要保存好,交给急救医生,这是再植的关键”。
“你有没有提前为(wèi)这些人再多做一步?”孙婧说(shuō),“我们的自我要求就是,不允许救援耽误在我身上。”
 “配合调度医生的询问,然后接受我们(wǒmen)的指导帮助”
5月10日8点刚过,接班的孙婧就(jiù)接到一个妈妈的电话,她一没留神,孩子吞东西(dōngxī)卡住了。
孙婧(sūnjìng)听到孩子哭得非常大声,她判断孩子气道应该是通畅的,但因为有明确的吞食异物史(shǐ),还是很有必要查看一下孩子的情况。
她特别希望对方能打开视频,这样她能直观地看到孩子的整体状态。“我需要看到孩子的情况,才能更准确(zhǔnquè)地判断。”孙婧补充(bǔchōng)道。
如今,有很多现代化的智慧应用让这场急救(jíjiù)接力提速。救护车(jiùhùchē)5G平台、短信精准定位以及视频(shìpín)医学指导功能,让120调度员能够更快速准确地获得(huòdé)患者定位,还可以通过视频直观地看到患者的情况,高效地帮助患者。
120会给求助者发送短信,只(zhǐ)需要点击短信中的视频邀请链接,调度医生、救护车组可以和(hé)病人实现三方视频通话。通过视频,他们(tāmen)做过不少成功的医学指导。
一名四五十岁的(de)男子,吃药丸时噎住了(le)。通过视频,姜宇婷指导家属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,成功了。
姚楠指导(zhǐdǎo)过一个躺卧位的海姆立克急救。患者因为吃鸡蛋羹呛到了,她指导家属操作,怎么都没成功。直到(zhídào)对方开了视频,姚楠才发现对方做错了,“他们一直在(zài)向下按,而不是向上推”。
“能视频通话(tōnghuà)了,我就能看见病人,我能告诉你怎么做。”姜宇婷说,但愿意(yuànyì)使用视频的求助者不多(duō)。有的家属担心隐私泄漏,有的是在公共场合,路人“不敢过去”。
在求助人身边(shēnbiān)的“第一目击者”的反应很(hěn)重要,有时甚至会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。
调度医生张震威接到(jiēdào)过(guò)一通电话,病人五六十岁,呼吸心跳骤停。他在调派系统上看到,附近就(jiù)有救护车,派车的同时,他想指导家属进行心肺复苏,但对方不配合,一直在哭喊。
另一个相似的情况(qíngkuàng)发生在北京市大兴区的一个地铁站,一个外地来出差的人突然倒地。这时,经过急救培训的地铁工作人员站了出来(chūlái),配合120调度医生指导,为病人做心肺(xīnfèi)复苏。120调度系统与AED(自动(zìdòng)体外除颤仪)电子地图(diànzidìtú)也(yě)已实现了联通,调度员指挥现场其他人员去取AED,很快,AED也用上了。现在这个病人完全康复,顺利出院。
陈敏瑞和同事们在(zài)很多场合呼吁,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掌握初级心肺复苏急救技能,在关键时刻“愿出手,能出手,敢(gǎn)出手”。
“请不要慌乱,不要尖叫和哭喊。”在张震威看来,家属最能帮到病人的(de)是保持冷静,“配合调度医生的询问(xúnwèn),然后接受(jiēshòu)我们的指导帮助”。
孙婧指导过一个二胎产妇在家分娩。电话那头告诉她(tā):爱人要生了,羊水(yángshuǐ)已经破了,能看见孩子的头了。对方十分冷静,语速比她接过的所有求助者都慢。孙婧耳朵贴着听筒使劲听,没有(méiyǒu)孕妇(yùnfù)疼痛的呻吟声,什么声音都没有。
“我当时也觉得有些(yǒuxiē)蹊跷。”她仍然按照调度系统医学指导模块里的(de)提示,一步步指导产妇用力,“尽自己应尽的义务”。
“孩子的头出来了(le)。”对方告诉她。孙婧(sūnjìng)告诉丈夫如何接住孩子,给孩子保暖等。这时,听到了孩子的哭声(kūshēng),孙婧才确信,自己确实成功指导了一个产妇分娩。
在医学(yīxué)指导时,调度医生要将复杂(fùzá)的(de)医学术语,转换成呼叫者听得懂、易于遵循的“指令”。对方听不懂“胸骨中下三分之一(sānfēnzhīyī)”,他们会翻译成“两乳头连线中点”;患者有时说“迷糊,嘴歪了,流哈喇子”,他们就会翻译成“可疑脑血管病”。
“你知道指导(zhǐdǎo)人心肺复苏活下来那种成就感,就像医院抢救活一个病人是(shì)一样的。”姚楠说,“还有,那种救护车到达现场(xiànchǎng)却找不着病人,我们联动啊、定位(dìngwèi)啊、查找要车记录啊,最终想方设法帮车组找着了,那种成就感跟救活一个人一样。”
“但有的家属不认可,他们认为调度员赶紧(gǎnjǐn)派车(chē)就行了,觉得进行医学指导说(shuō)这说那的是在耽误救治时间。”陈敏瑞解释(jiěshì),“其实,我们的流程是先派出救护车,随后调度员再询问详细情况,给呼救(hūjiù)者做医学指导,不会影响救护车驶向现场。我们的目标是实现‘呼救即急救’,最大限度地为挽救生命争取时间。”
还有的(de)情况是,拨通120时,患者虽然没有发生心搏骤停,但也会特别(tèbié)提醒,“在救护车(jiùhùchē)到达之前,注意保持患者呼吸道通畅,观察患者,一旦出现病情变化,一定要再次拨打(bōdǎ)120,我们给您医学指导”。
“但一些家属没有这个意识。”陈敏瑞说,在等救护车的(de)过程中,有的家属急着给患者(huànzhě)找药,观察不到病人的情况。有时家属对药物也不是很了解,就给患者服用,可能会因用药不当加重病情,甚至影响(yǐngxiǎng)后续的专业救治(jiùzhì)。
那些“电话那头(nàtóu)的(de)人一直在哭,说不清地址,只说‘快点儿来’”的求助电话,几乎令所有调度医生焦虑(jiāolǜ)。屏幕上的读秒器走过一秒,意味着救援时间又被拖了一秒。
在北京,音为“jia yuan”的小区至少可以(kěyǐ)指向9个地方。对调度医生来说,有时问清地名就是(jiùshì)最困难的事。
有的老人遇到突发情况会慌,什么都想不起来(xiǎngbùqǐlái)。调度(diàodù)员会开启引导模式问话:“您家附近有什么明显的标志建筑?离您家最近的医院是哪?走着就能到吗?”因为老人常开药,如果能报出(bàochū)卫生站的名字,范围会缩小(suōxiǎo)。这倚赖调度医生的经验。
把电脑上的地图放大,电话这头开始念小区名字(míngzì),把附近的逐个排除。确认了小区,再(zài)到楼号和门牌号,他们一点点问。
有时求助电话(diànhuà)来自居住在北京(běijīng)的外国人。调度员会借助北京多语言服务平台,在外语志愿者的协助下,共同完成和(hé)外国人的准确沟通,迅速派车。
但有一次,救护车派出去了,转了好几圈也没能找到人。陈敏瑞通过加微信,对方发送定位(dìngwèi)引导,也还是找不到。所有人都在焦急等待(děngdài)。
“永不言弃,我们就是这样。”她让对方打开手机的手电筒,在窗户旁一直晃。车组看到(kàndào)了,在那几十幢楼的小区里(lǐ),他们终于“捞(lāo)”到了人。
对于老人或年轻人独居的家庭,孙婧建议“尽量(jǐnliàng)用密码锁”“在不涉及隐私的地方安上(ānshàng)摄像头”。
她接过的电话里,有老人(lǎorén)摔倒在家里,开不了门(mén),需要119同时到达破拆。还有的是子女发现家中老人两个小时都没有到客厅活动过,他用监控呼叫,也没有反应,然后(ránhòu)拨打了120。救护车组及时(jíshí)赶到,救下了天然气中毒的老人。
还有独居的(de)女孩在卫生间意外摔倒,动弹不得。她尝试唤醒了(le)智能手机,拨打120。陈敏瑞接到(jiēdào)了这通求救电话。电话那头的声音若隐若无,她集中精力,耳朵(ěrduǒ)贴紧耳机,大声与对方交流。问清了地址和门锁的密码,急救人员顺利来到女孩身边救治。
调度医生们习惯将日常受理的真实(zhēnshí)急救呼救案例记下来,有(yǒu)的画成漫画(mànhuà),有的发在120官方公众号宣传推广,让社会公众学到简单的医学急救常识,提升急救意识和健康素养。
“配合调度医生的询问,然后接受我们(wǒmen)的指导帮助”
5月10日8点刚过,接班的孙婧就(jiù)接到一个妈妈的电话,她一没留神,孩子吞东西(dōngxī)卡住了。
孙婧(sūnjìng)听到孩子哭得非常大声,她判断孩子气道应该是通畅的,但因为有明确的吞食异物史(shǐ),还是很有必要查看一下孩子的情况。
她特别希望对方能打开视频,这样她能直观地看到孩子的整体状态。“我需要看到孩子的情况,才能更准确(zhǔnquè)地判断。”孙婧补充(bǔchōng)道。
如今,有很多现代化的智慧应用让这场急救(jíjiù)接力提速。救护车(jiùhùchē)5G平台、短信精准定位以及视频(shìpín)医学指导功能,让120调度员能够更快速准确地获得(huòdé)患者定位,还可以通过视频直观地看到患者的情况,高效地帮助患者。
120会给求助者发送短信,只(zhǐ)需要点击短信中的视频邀请链接,调度医生、救护车组可以和(hé)病人实现三方视频通话。通过视频,他们(tāmen)做过不少成功的医学指导。
一名四五十岁的(de)男子,吃药丸时噎住了(le)。通过视频,姜宇婷指导家属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,成功了。
姚楠指导(zhǐdǎo)过一个躺卧位的海姆立克急救。患者因为吃鸡蛋羹呛到了,她指导家属操作,怎么都没成功。直到(zhídào)对方开了视频,姚楠才发现对方做错了,“他们一直在(zài)向下按,而不是向上推”。
“能视频通话(tōnghuà)了,我就能看见病人,我能告诉你怎么做。”姜宇婷说,但愿意(yuànyì)使用视频的求助者不多(duō)。有的家属担心隐私泄漏,有的是在公共场合,路人“不敢过去”。
在求助人身边(shēnbiān)的“第一目击者”的反应很(hěn)重要,有时甚至会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。
调度医生张震威接到(jiēdào)过(guò)一通电话,病人五六十岁,呼吸心跳骤停。他在调派系统上看到,附近就(jiù)有救护车,派车的同时,他想指导家属进行心肺复苏,但对方不配合,一直在哭喊。
另一个相似的情况(qíngkuàng)发生在北京市大兴区的一个地铁站,一个外地来出差的人突然倒地。这时,经过急救培训的地铁工作人员站了出来(chūlái),配合120调度医生指导,为病人做心肺(xīnfèi)复苏。120调度系统与AED(自动(zìdòng)体外除颤仪)电子地图(diànzidìtú)也(yě)已实现了联通,调度员指挥现场其他人员去取AED,很快,AED也用上了。现在这个病人完全康复,顺利出院。
陈敏瑞和同事们在(zài)很多场合呼吁,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掌握初级心肺复苏急救技能,在关键时刻“愿出手,能出手,敢(gǎn)出手”。
“请不要慌乱,不要尖叫和哭喊。”在张震威看来,家属最能帮到病人的(de)是保持冷静,“配合调度医生的询问(xúnwèn),然后接受(jiēshòu)我们的指导帮助”。
孙婧指导过一个二胎产妇在家分娩。电话那头告诉她(tā):爱人要生了,羊水(yángshuǐ)已经破了,能看见孩子的头了。对方十分冷静,语速比她接过的所有求助者都慢。孙婧耳朵贴着听筒使劲听,没有(méiyǒu)孕妇(yùnfù)疼痛的呻吟声,什么声音都没有。
“我当时也觉得有些(yǒuxiē)蹊跷。”她仍然按照调度系统医学指导模块里的(de)提示,一步步指导产妇用力,“尽自己应尽的义务”。
“孩子的头出来了(le)。”对方告诉她。孙婧(sūnjìng)告诉丈夫如何接住孩子,给孩子保暖等。这时,听到了孩子的哭声(kūshēng),孙婧才确信,自己确实成功指导了一个产妇分娩。
在医学(yīxué)指导时,调度医生要将复杂(fùzá)的(de)医学术语,转换成呼叫者听得懂、易于遵循的“指令”。对方听不懂“胸骨中下三分之一(sānfēnzhīyī)”,他们会翻译成“两乳头连线中点”;患者有时说“迷糊,嘴歪了,流哈喇子”,他们就会翻译成“可疑脑血管病”。
“你知道指导(zhǐdǎo)人心肺复苏活下来那种成就感,就像医院抢救活一个病人是(shì)一样的。”姚楠说,“还有,那种救护车到达现场(xiànchǎng)却找不着病人,我们联动啊、定位(dìngwèi)啊、查找要车记录啊,最终想方设法帮车组找着了,那种成就感跟救活一个人一样。”
“但有的家属不认可,他们认为调度员赶紧(gǎnjǐn)派车(chē)就行了,觉得进行医学指导说(shuō)这说那的是在耽误救治时间。”陈敏瑞解释(jiěshì),“其实,我们的流程是先派出救护车,随后调度员再询问详细情况,给呼救(hūjiù)者做医学指导,不会影响救护车驶向现场。我们的目标是实现‘呼救即急救’,最大限度地为挽救生命争取时间。”
还有的(de)情况是,拨通120时,患者虽然没有发生心搏骤停,但也会特别(tèbié)提醒,“在救护车(jiùhùchē)到达之前,注意保持患者呼吸道通畅,观察患者,一旦出现病情变化,一定要再次拨打(bōdǎ)120,我们给您医学指导”。
“但一些家属没有这个意识。”陈敏瑞说,在等救护车的(de)过程中,有的家属急着给患者(huànzhě)找药,观察不到病人的情况。有时家属对药物也不是很了解,就给患者服用,可能会因用药不当加重病情,甚至影响(yǐngxiǎng)后续的专业救治(jiùzhì)。
那些“电话那头(nàtóu)的(de)人一直在哭,说不清地址,只说‘快点儿来’”的求助电话,几乎令所有调度医生焦虑(jiāolǜ)。屏幕上的读秒器走过一秒,意味着救援时间又被拖了一秒。
在北京,音为“jia yuan”的小区至少可以(kěyǐ)指向9个地方。对调度医生来说,有时问清地名就是(jiùshì)最困难的事。
有的老人遇到突发情况会慌,什么都想不起来(xiǎngbùqǐlái)。调度(diàodù)员会开启引导模式问话:“您家附近有什么明显的标志建筑?离您家最近的医院是哪?走着就能到吗?”因为老人常开药,如果能报出(bàochū)卫生站的名字,范围会缩小(suōxiǎo)。这倚赖调度医生的经验。
把电脑上的地图放大,电话这头开始念小区名字(míngzì),把附近的逐个排除。确认了小区,再(zài)到楼号和门牌号,他们一点点问。
有时求助电话(diànhuà)来自居住在北京(běijīng)的外国人。调度员会借助北京多语言服务平台,在外语志愿者的协助下,共同完成和(hé)外国人的准确沟通,迅速派车。
但有一次,救护车派出去了,转了好几圈也没能找到人。陈敏瑞通过加微信,对方发送定位(dìngwèi)引导,也还是找不到。所有人都在焦急等待(děngdài)。
“永不言弃,我们就是这样。”她让对方打开手机的手电筒,在窗户旁一直晃。车组看到(kàndào)了,在那几十幢楼的小区里(lǐ),他们终于“捞(lāo)”到了人。
对于老人或年轻人独居的家庭,孙婧建议“尽量(jǐnliàng)用密码锁”“在不涉及隐私的地方安上(ānshàng)摄像头”。
她接过的电话里,有老人(lǎorén)摔倒在家里,开不了门(mén),需要119同时到达破拆。还有的是子女发现家中老人两个小时都没有到客厅活动过,他用监控呼叫,也没有反应,然后(ránhòu)拨打了120。救护车组及时(jíshí)赶到,救下了天然气中毒的老人。
还有独居的(de)女孩在卫生间意外摔倒,动弹不得。她尝试唤醒了(le)智能手机,拨打120。陈敏瑞接到(jiēdào)了这通求救电话。电话那头的声音若隐若无,她集中精力,耳朵(ěrduǒ)贴紧耳机,大声与对方交流。问清了地址和门锁的密码,急救人员顺利来到女孩身边救治。
调度医生们习惯将日常受理的真实(zhēnshí)急救呼救案例记下来,有(yǒu)的画成漫画(mànhuà),有的发在120官方公众号宣传推广,让社会公众学到简单的医学急救常识,提升急救意识和健康素养。



 北京急救中心调度医生狄珊珊利用业余时间绘制漫画,普及急救相关知识(zhīshí)。狄珊珊绘(díshānshānhuì)
“没有什么比生命更(gèng)重要”
在(zài)陈敏瑞看来,生命很脆弱,一场意外、一次冲动可能就会让它凋零;但(dàn)又很顽强,只要及时正确施救,就有可能从死神手里抢回生机。
有时(yǒushí)不幸和幸运同时出现在一套(yītào)合租房中。隔壁的人烧炭轻生,一氧化碳也飘进了住着年轻女孩的另一间房。
女孩的朋友联系不上(bùshàng)她,打了110和120,救护车和警车同时赶到。他们发现女孩有意识,有点小便失禁,没有人知道原因(yuányīn),因为及时送到(sòngdào)医院,女孩得救了。
4个(gè)小时后,同一地址又有(yǒu)警察要车。那个轻生的人被发现,房东报了警,但太晚了。
陈敏瑞接过一通电话,一个14岁的男孩关上自己(zìjǐ)的房门,发生(fāshēng)了意外,等家里人发现时,已经没了心跳和呼吸。
她派出救护车,同时开始心肺复苏的指导。“1,2,3,4……”她数着节奏,每30下停一次,指导情绪(qíngxù)崩溃的母亲为孩子做(zuò)人工呼吸,然后再继续按压(ànyā)。
你很希望(xīwàng)孩子活,可是你明知道他活不了,但是(dànshì)你必须把希望告诉他母亲——“你不做就没有希望,请配合我们的指导。”陈敏瑞能体会(tǐhuì)到电话那头母亲的感受,孩子小的时候,她最怕接到家里(jiālǐ)的电话,“打电话就是有事,大多是孩子的事”。
几乎每个调度医生都有不少成功指导心肺复苏的(de)(de)案例。陈敏瑞清楚记得,一个冬天,一位女士给60岁(suì)的父亲叫救护车,作为家属,她看到了父亲倒地,心跳呼吸都没有了。
老人的(de)女儿、妻子配合(pèihé)电话这端的陈敏瑞,给患者做心肺复苏。救护车(jiùhùchē)组到现场时,患者呼吸心跳恢复,有了(le)意识。后来,医院确诊为脑梗,因为抓住了救命的“黄金4分钟”,患者出院后恢复得非常好。“这是特别成功的一个案例。”
但这次,陈敏瑞没能(méinéng)成功。她(tā)忘不了那个没救回来的14岁男孩和那位在她指导下不断重复急救动作的母亲。
工作中的(de)事她都愿意和孩子讲。陈敏瑞想把这些案例(ànlì)分享给孩子,但同在医疗系统工作的丈夫有些顾虑。
“我是(shì)想让孩子知道,没有(méiyǒu)什么比生命更重要,一个冲动性的行为就没有机会了,没有以后了。”陈敏瑞说。
孙婧(sūnjìng)和丈夫都在120上班,所有的法定假日,她和丈夫都不能请假离开工作属地,需要随时(suíshí)待命。
他们对女儿感到亏欠。相比于绘本上的晚安故事,女儿对妈妈的工作(gōngzuò)更好奇,“你今天接了什么(shénme)电话?讲(jiǎng)来听听。”“我说你从小就听悲欢离合,这真的好吗?”她觉得女儿不缺爱和死亡教育。
如果当天“风平浪静”,孙婧就得(dé)搜肠刮肚找一些不寻常的逻辑,或是有意思的见闻。但(dàn)她希望“每一天都风平浪静”。
她(tā)也偶尔会抱怨这份工作太累、神经太紧绷(jǐnbēng),但更多时候,她把自己对这份职业的认同与自豪感也传递给(gěi)孩子。“不要在意有没有人看到你,要看到你在这件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,自己问心无愧就好了。”
陈敏瑞依然每天对着电话重复一百多遍“您好,北京120!”,她的任务是将救护车调派到(diàopàidào)有(yǒu)急救需求的呼救者身边。
陈敏瑞说,“守好这条电话线,我能为后面的(de)抢救(qiǎngjiù)多争取出来两分钟,这两分钟或许就是一条生命。”
北京急救中心调度医生狄珊珊利用业余时间绘制漫画,普及急救相关知识(zhīshí)。狄珊珊绘(díshānshānhuì)
“没有什么比生命更(gèng)重要”
在(zài)陈敏瑞看来,生命很脆弱,一场意外、一次冲动可能就会让它凋零;但(dàn)又很顽强,只要及时正确施救,就有可能从死神手里抢回生机。
有时(yǒushí)不幸和幸运同时出现在一套(yītào)合租房中。隔壁的人烧炭轻生,一氧化碳也飘进了住着年轻女孩的另一间房。
女孩的朋友联系不上(bùshàng)她,打了110和120,救护车和警车同时赶到。他们发现女孩有意识,有点小便失禁,没有人知道原因(yuányīn),因为及时送到(sòngdào)医院,女孩得救了。
4个(gè)小时后,同一地址又有(yǒu)警察要车。那个轻生的人被发现,房东报了警,但太晚了。
陈敏瑞接过一通电话,一个14岁的男孩关上自己(zìjǐ)的房门,发生(fāshēng)了意外,等家里人发现时,已经没了心跳和呼吸。
她派出救护车,同时开始心肺复苏的指导。“1,2,3,4……”她数着节奏,每30下停一次,指导情绪(qíngxù)崩溃的母亲为孩子做(zuò)人工呼吸,然后再继续按压(ànyā)。
你很希望(xīwàng)孩子活,可是你明知道他活不了,但是(dànshì)你必须把希望告诉他母亲——“你不做就没有希望,请配合我们的指导。”陈敏瑞能体会(tǐhuì)到电话那头母亲的感受,孩子小的时候,她最怕接到家里(jiālǐ)的电话,“打电话就是有事,大多是孩子的事”。
几乎每个调度医生都有不少成功指导心肺复苏的(de)(de)案例。陈敏瑞清楚记得,一个冬天,一位女士给60岁(suì)的父亲叫救护车,作为家属,她看到了父亲倒地,心跳呼吸都没有了。
老人的(de)女儿、妻子配合(pèihé)电话这端的陈敏瑞,给患者做心肺复苏。救护车(jiùhùchē)组到现场时,患者呼吸心跳恢复,有了(le)意识。后来,医院确诊为脑梗,因为抓住了救命的“黄金4分钟”,患者出院后恢复得非常好。“这是特别成功的一个案例。”
但这次,陈敏瑞没能(méinéng)成功。她(tā)忘不了那个没救回来的14岁男孩和那位在她指导下不断重复急救动作的母亲。
工作中的(de)事她都愿意和孩子讲。陈敏瑞想把这些案例(ànlì)分享给孩子,但同在医疗系统工作的丈夫有些顾虑。
“我是(shì)想让孩子知道,没有(méiyǒu)什么比生命更重要,一个冲动性的行为就没有机会了,没有以后了。”陈敏瑞说。
孙婧(sūnjìng)和丈夫都在120上班,所有的法定假日,她和丈夫都不能请假离开工作属地,需要随时(suíshí)待命。
他们对女儿感到亏欠。相比于绘本上的晚安故事,女儿对妈妈的工作(gōngzuò)更好奇,“你今天接了什么(shénme)电话?讲(jiǎng)来听听。”“我说你从小就听悲欢离合,这真的好吗?”她觉得女儿不缺爱和死亡教育。
如果当天“风平浪静”,孙婧就得(dé)搜肠刮肚找一些不寻常的逻辑,或是有意思的见闻。但(dàn)她希望“每一天都风平浪静”。
她(tā)也偶尔会抱怨这份工作太累、神经太紧绷(jǐnbēng),但更多时候,她把自己对这份职业的认同与自豪感也传递给(gěi)孩子。“不要在意有没有人看到你,要看到你在这件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,自己问心无愧就好了。”
陈敏瑞依然每天对着电话重复一百多遍“您好,北京120!”,她的任务是将救护车调派到(diàopàidào)有(yǒu)急救需求的呼救者身边。
陈敏瑞说,“守好这条电话线,我能为后面的(de)抢救(qiǎngjiù)多争取出来两分钟,这两分钟或许就是一条生命。”
 20世纪80年代调度(diàodù)台。
20世纪80年代调度(diàodù)台。
 北京120调度(diàodù)指挥中心。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刚成为医学生(yīxuéshēng)那会儿,这些年轻人没想过毕业之后(zhīhòu)“去120接电话”。
他们接的每一通电话(tōngdiànhuà)都很紧急:孩子呛奶窒息(zhìxī),老人失去意识昏迷,产妇在家临产,危重病人需要转院,还有车祸、火情,以及一座常住人口超过2100万的超大城市里(lǐ)的各种突发状况。
在北京,平均(píngjūn)每30秒就有一辆120救护车接到(jiēdào)这里的(de)指令,驶向救人的现场。三十多年来,北京急救中心调度大厅的调度岗(gǎng)席位从3个增至30多个,急救调度员的声音此起彼伏——“您好,120,需要救护车吗?”
他们的(de)实际角色是“调度医生”,脑子里装着整个北京市的地图和400多个急救站点的位置。在(zài)派出的急救车组到达之前,他们会(huì)通过电话远程指导家属或好心的陌生人(mòshēngrén),给孩子解除气道异物梗阻、给产妇接生、给心搏骤停的患者做心肺复苏。
一个临床医学专业(zhuānyè)的120调度医生,工作(gōngzuò)了二十几年,没给病人开过一张处方,却“救活过许多人”。
在危重紧急的现场,两辆(liǎngliàng)摩托开着(kāizhe)警笛为急救车开道,医院(yīyuàn)早已建好绿色通道等待。少有人知道(zhīdào),120的调度医生人虽不在现场,却可以协调119、110、122“警医联动”,一键启动联合救援,共同完成挽救生命的艰巨任务。
从120电话接通的那一刻起,一场急救(jíjiù)接力就(jiù)开始了。毫无疑问,调度医生们手握着的是生命线上的急救“第一棒”。
北京120调度(diàodù)指挥中心。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刚成为医学生(yīxuéshēng)那会儿,这些年轻人没想过毕业之后(zhīhòu)“去120接电话”。
他们接的每一通电话(tōngdiànhuà)都很紧急:孩子呛奶窒息(zhìxī),老人失去意识昏迷,产妇在家临产,危重病人需要转院,还有车祸、火情,以及一座常住人口超过2100万的超大城市里(lǐ)的各种突发状况。
在北京,平均(píngjūn)每30秒就有一辆120救护车接到(jiēdào)这里的(de)指令,驶向救人的现场。三十多年来,北京急救中心调度大厅的调度岗(gǎng)席位从3个增至30多个,急救调度员的声音此起彼伏——“您好,120,需要救护车吗?”
他们的(de)实际角色是“调度医生”,脑子里装着整个北京市的地图和400多个急救站点的位置。在(zài)派出的急救车组到达之前,他们会(huì)通过电话远程指导家属或好心的陌生人(mòshēngrén),给孩子解除气道异物梗阻、给产妇接生、给心搏骤停的患者做心肺复苏。
一个临床医学专业(zhuānyè)的120调度医生,工作(gōngzuò)了二十几年,没给病人开过一张处方,却“救活过许多人”。
在危重紧急的现场,两辆(liǎngliàng)摩托开着(kāizhe)警笛为急救车开道,医院(yīyuàn)早已建好绿色通道等待。少有人知道(zhīdào),120的调度医生人虽不在现场,却可以协调119、110、122“警医联动”,一键启动联合救援,共同完成挽救生命的艰巨任务。
从120电话接通的那一刻起,一场急救(jíjiù)接力就(jiù)开始了。毫无疑问,调度医生们手握着的是生命线上的急救“第一棒”。
 院前医疗救治转运(zhuǎnyùn)危重症患者。
“从两分钟缩短到(dào)90秒,然后是1分钟,有时仅需50秒”
5月一个雨天的上午10点,北京(běijīng)有433辆救护车正在执行任务。
在调度员姜宇婷面前的电脑屏幕(diànnǎopíngmù)上,一些被标记为红色的救护车图标代表正在执行任务(rènwù)中,此时穿梭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救护车有21辆车是她派出去(qù)的。
工作(gōngzuò)进入第十个年头,她不会“在上班的前一天就开始紧张了”,但也没办法放松下来。“这是一个没办法松弛的工作,需要精神高度集中,绝不能(juébùnéng)出错(chūcuò)。”姜宇婷补充说,“出错就可能是人命”。
和(hé)大部分急救调度员一样,来120上班前,她对(duì)这项工作一无所知,而现在“对这份职责和使命却有了深刻的体会”。
孙婧学的是临床医学(línchuángyīxué),从事急救调度工作后她发现,“每天都有一百多种焦虑从电话那端传来”。工作快(kuài)20年,只要电话那头的语速一快,她的精神马上(mǎshàng)就会“跟着‘跑’起来”。
职业经验(jīngyàn)让她学会保持冷静并让对方“淡定降速”,在她的引导下(xià)完成有效(yǒuxiào)信息采集。“我必须专业,问出重点,才能迅速调派救护车开展救治。”孙婧说。
上岗的前(qián)几个月,新来的年轻人打字(dǎzì)要练,地图要背,说话都要学,这是“最基础的基本功”。
为了更快地背下那些环路和桥,姜宇婷按老调度的(de)经验(jīngyàn),歇班的日子就坐(zuò)公交车在北京环路上一圈圈地转。考核时,他们要在部分空白的地图上,填上路名和桥名。
穿着胸前和后背处印着蓝色“北京120急救”的白色工作服,姜宇婷戴着麦克风和听筒在同一侧的耳机,和师傅姚楠接入同一台电话,她(tā)只能听。这部电话会(diànhuàhuì)一点点(yìdiǎndiǎn)移交给她。
除了吃饭和(hé)去厕所,耳机不能摘,保证(bǎozhèng)电话进来时立即能接听。科里的规定是“10秒内接听电话”。
两通电话的间隙,偶尔(ǒuěr)有医生站起来做做扩胸运动,或者扭扭(niǔniǔ)腰。他们每班12个小时,久坐可能让他们的腰肌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。调度大厅外的墙壁(qiángbì)上贴着一张《预防腰椎间盘突出症需要(xūyào)注意哪些事项》,每名调度医生上下班等电梯时都能“温习一遍”。
姚楠的左耳被压在听筒下25年,除了听对方说话,还要识别背景音(yīn)——急促的呼吸声、喘鸣声或是异样的鼾声。她现在偶尔觉得听得不够清楚,常换到另一只“非惯用(guànyòng)耳”。但(dàn)没多久又换回来(huànhuílái),她嫌“另一只耳朵业务不够熟练”。
姚楠2001年入(niánrù)职,那时移动互联网刚萌芽,乔布斯的(de)第一代苹果手机要在6年后出现,中国的3G网络建设还要再晚一年启动。
和她同批(tóngpī)的调度医生入(rù)职时,电脑还没装完。他们背地图,背站点电话,学习五笔输入法,人手(rénshǒu)一本科里调度医生们自己编写的《医学指南》,在遇到突发情况时给出准确的医学指导。
如今,北京(běijīng)急救中心自主研发了更贴合(tiēhé)国情的高级调度在线生命支持系统ADLS——在调度席位的电脑里,每当他们输入病人的情况,就可以得到分步骤的医学指导,调度员可以依此对病人进行(jìnxíng)快速规范(guīfàn)的医学指导。
120调度系统(xìtǒng)也经历了好几代的升级改造。每个调度员面前有3块电脑屏幕:左边(zuǒbiān)是(shì)地图,中间是登记信息的受理屏,右边是车辆(chēliàng)信息。今年年初,他们接入了语音呼叫系统,只要求助者说清楚了姓名、地址和病情,他们点个按钮,待命的救护车就会接到出发指令。
系统还在持续优化。“我们主任老说(shuō),你(nǐ)是调度,有没有思考过如何让急救事业更往前发展一步?”孙婧笑着说,“好‘卷’是不是?”
每个月,他们都会统计这个月科里和每名调度员(diàodùyuán)派车的平均秒数。在技术和算法的支撑下,过去几年,派车时间从两分钟(liǎngfēnzhōng)缩短到(dào)90秒,然后是1分钟,有时仅需50秒。
50秒内,他们(tāmen)要做的事情太多了。
院前医疗救治转运(zhuǎnyùn)危重症患者。
“从两分钟缩短到(dào)90秒,然后是1分钟,有时仅需50秒”
5月一个雨天的上午10点,北京(běijīng)有433辆救护车正在执行任务。
在调度员姜宇婷面前的电脑屏幕(diànnǎopíngmù)上,一些被标记为红色的救护车图标代表正在执行任务(rènwù)中,此时穿梭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救护车有21辆车是她派出去(qù)的。
工作(gōngzuò)进入第十个年头,她不会“在上班的前一天就开始紧张了”,但也没办法放松下来。“这是一个没办法松弛的工作,需要精神高度集中,绝不能(juébùnéng)出错(chūcuò)。”姜宇婷补充说,“出错就可能是人命”。
和(hé)大部分急救调度员一样,来120上班前,她对(duì)这项工作一无所知,而现在“对这份职责和使命却有了深刻的体会”。
孙婧学的是临床医学(línchuángyīxué),从事急救调度工作后她发现,“每天都有一百多种焦虑从电话那端传来”。工作快(kuài)20年,只要电话那头的语速一快,她的精神马上(mǎshàng)就会“跟着‘跑’起来”。
职业经验(jīngyàn)让她学会保持冷静并让对方“淡定降速”,在她的引导下(xià)完成有效(yǒuxiào)信息采集。“我必须专业,问出重点,才能迅速调派救护车开展救治。”孙婧说。
上岗的前(qián)几个月,新来的年轻人打字(dǎzì)要练,地图要背,说话都要学,这是“最基础的基本功”。
为了更快地背下那些环路和桥,姜宇婷按老调度的(de)经验(jīngyàn),歇班的日子就坐(zuò)公交车在北京环路上一圈圈地转。考核时,他们要在部分空白的地图上,填上路名和桥名。
穿着胸前和后背处印着蓝色“北京120急救”的白色工作服,姜宇婷戴着麦克风和听筒在同一侧的耳机,和师傅姚楠接入同一台电话,她(tā)只能听。这部电话会(diànhuàhuì)一点点(yìdiǎndiǎn)移交给她。
除了吃饭和(hé)去厕所,耳机不能摘,保证(bǎozhèng)电话进来时立即能接听。科里的规定是“10秒内接听电话”。
两通电话的间隙,偶尔(ǒuěr)有医生站起来做做扩胸运动,或者扭扭(niǔniǔ)腰。他们每班12个小时,久坐可能让他们的腰肌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。调度大厅外的墙壁(qiángbì)上贴着一张《预防腰椎间盘突出症需要(xūyào)注意哪些事项》,每名调度医生上下班等电梯时都能“温习一遍”。
姚楠的左耳被压在听筒下25年,除了听对方说话,还要识别背景音(yīn)——急促的呼吸声、喘鸣声或是异样的鼾声。她现在偶尔觉得听得不够清楚,常换到另一只“非惯用(guànyòng)耳”。但(dàn)没多久又换回来(huànhuílái),她嫌“另一只耳朵业务不够熟练”。
姚楠2001年入(niánrù)职,那时移动互联网刚萌芽,乔布斯的(de)第一代苹果手机要在6年后出现,中国的3G网络建设还要再晚一年启动。
和她同批(tóngpī)的调度医生入(rù)职时,电脑还没装完。他们背地图,背站点电话,学习五笔输入法,人手(rénshǒu)一本科里调度医生们自己编写的《医学指南》,在遇到突发情况时给出准确的医学指导。
如今,北京(běijīng)急救中心自主研发了更贴合(tiēhé)国情的高级调度在线生命支持系统ADLS——在调度席位的电脑里,每当他们输入病人的情况,就可以得到分步骤的医学指导,调度员可以依此对病人进行(jìnxíng)快速规范(guīfàn)的医学指导。
120调度系统(xìtǒng)也经历了好几代的升级改造。每个调度员面前有3块电脑屏幕:左边(zuǒbiān)是(shì)地图,中间是登记信息的受理屏,右边是车辆(chēliàng)信息。今年年初,他们接入了语音呼叫系统,只要求助者说清楚了姓名、地址和病情,他们点个按钮,待命的救护车就会接到出发指令。
系统还在持续优化。“我们主任老说(shuō),你(nǐ)是调度,有没有思考过如何让急救事业更往前发展一步?”孙婧笑着说,“好‘卷’是不是?”
每个月,他们都会统计这个月科里和每名调度员(diàodùyuán)派车的平均秒数。在技术和算法的支撑下,过去几年,派车时间从两分钟(liǎngfēnzhōng)缩短到(dào)90秒,然后是1分钟,有时仅需50秒。
50秒内,他们(tāmen)要做的事情太多了。
 陈敏瑞(左一)和孙婧(右一)防汛应急(yìngjí)期间调度指挥。
调度医生(yīshēng)心里准备的若干个问题就像“肌肉记忆”
120急救没有(méiyǒu)“淡旺季”之分。
春天,过敏引起(yǐnqǐ)的哮喘患者多;夏天,热射病的发病(fābìng)人数上升(shàngshēng);城市煤改气前,一到冬天,总有一氧化碳中毒的。换季时,中老年容易突发心脑血管疾病。赶上节假日、雨雪天气,摔伤(shuāishāng)的、车祸的120呼叫量有所增多。
技术和算法让系统可以协助(xiézhù)派车。10年前他们按行政区域派车,2015年,北京市成为全国唯一实现(shíxiàn)统一指挥、一级调度的城市,无论呼救(hūjiù)者身处区域内何处拨打(bōdǎ)120,都会按照卫星定位就近调派救护车辆。
系统有时没有人聪明。120调度员就像急救网络的“神经中枢”,“精准统筹和动态调派急救力量”。救护车的配置和随车医生的资质与能力(nénglì)(nénglì)都(dōu)有统一要求,但还是会有呼吸机(hūxījī)、微量泵等“选配”器材的差别,医生的救治能力和经验值也不相同,这就需要(xūyào)调度员针对不同急危重程度的情况,人工指派相应急救车组。
“调度员(diàodùyuán)发出的派车(chē)指令就是院前急救人员的命令。”陈敏瑞觉得,对于调度员,“果断非常重要”。
120调度工作有着极为严格的质控要求,他们接听的每一通电话都可能接受复盘检查。通话录音会被多方反复(fǎnfù)审听,逻辑是否闭环,任务是否调派准确。甚至是,每一句话的语音语调是否合适——要照顾(zhàogù)求助者的情绪,调度医生(yīshēng)有很多“不能说(shuō)的话”,比如“打断一下”“说清楚点,你说不清楚能不能换个人(gèrén)说”。
一次车祸,公交车上七八个人受伤,陈敏瑞在(zài)第一时间先派出4辆救护车——“问清现场伤员情况,几个人躺(tǎng)着不能动,几个人可以坐着,初步判断出伤情(shāngqíng)的严重程度,明确派车数量。”她解释,根据现场情况,调度员按照(ànzhào)工作预案随时增援,会动态调整急救力量。
某次紧急任务,陈敏瑞派出几十辆救护车(jiùhùchē)。几名调度(diàodù)员组成调度专席——每辆车都要盯,接几个人,伤情(shāngqíng)是(shì)什么样的,准备送哪个医院,需要与哪些医院提前建立绿色通道等。同时,他们还要向车组及时通报路况。
突发事件(tūfāshìjiàn)的数据(shùjù)要时时统计更新,有多少人受伤,派出多少车辆,送去了哪些医院……调度员必须能准确地回答出来。
孙婧回忆,那次突发事件延续到了她下班时间,交接好工作后,她也不敢把手机调到静音,始终保持待命状态。因为家离单位近,她是工作预案里应急(yìngjí)队伍的“第一(dìyī)梯队”。她知道不一定(yídìng)会叫她,但她“做好了随时(suíshí)上班的准备”。
经验让她预判了情况(qíngkuàng)的复杂性。她是经历(jīnglì)过好几场火灾救援的调度员(diàodùyuán)。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,她听到“800兆”对讲机里119的直接呼叫,拿起手台之前“脑瓜子就嗡嗡的”。
一场大风造成了平房(píngfáng)起火,她的标准问题是:平房是联排吗?都有人(yǒurén)住吗?火还在烧吗?早些年,“回”型楼里(lóulǐ)的群租房着火,大火转着圈地烧。她“要对事情(shìqíng)有预判,会演变成什么情况,就一定要派足量的车”。
交通事故现场比较复杂,现场多人(duōrén)打电话进来,每名调度医生的屏幕上(shàng)都会显示此刻用车需求的位置。他们在调度大厅里会互通信息,组长要(yào)综合判断处理。
同样是客车发生事故,情况也不一样:和什么相撞?满载还是空载(kōngzài)?几个人受伤?有没有人员被困?撞击之后车辆有没有起火……调度医生心里准备的若干个问题就像“肌肉记忆”,要在第一通电话(diànhuà)(tōngdiànhuà)时“一把问清”,因为后续电话可能很难再接通(jiētōng)了。
“一把问清(wènqīng)”考察了他们的能力。大型商场或者多路换乘的地铁站,孙婧会在第一时间(shíjiān)问清楚,哪个入口离现场最近(zuìjìn),直梯在哪里——医生的急救包重10公斤,担架床需要直梯。她(tā)必须为车组确认找到病人的最快路线。
即便救护车到达现场了,他们的(de)工作还没完。遇到危重紧急的情况(qíngkuàng),有时需要110警察配合(pèihé),需要联动122交通部门(jiāotōngbùmén)在设定的路上为救护车清路,需要与附近接治医院提前建立绿色通道,环环相扣,都需要调度医生协调处理。
组长(zǔzhǎng)席上放着“四台联动”——110、120、119、122之间建立了(le)联动机制。调度医生可以用“800兆”对讲机直接呼叫,开启三方通话(tōnghuà)。
有家长在商场里(lǐ)拨打120,孩子(háizi)的(de)(de)3根手指被意外碾断。接电话的几秒钟,陈敏瑞想了“特别多关于孩子今后的工作和生活(的场景)”。“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就近派车,建立绿色通道,缩短(suōduǎn)孩子就诊时间。”她不忘嘱咐家长“断指一定要保存好,交给急救医生,这是再植的关键”。
“你有没有提前为(wèi)这些人再多做一步?”孙婧说(shuō),“我们的自我要求就是,不允许救援耽误在我身上。”
陈敏瑞(左一)和孙婧(右一)防汛应急(yìngjí)期间调度指挥。
调度医生(yīshēng)心里准备的若干个问题就像“肌肉记忆”
120急救没有(méiyǒu)“淡旺季”之分。
春天,过敏引起(yǐnqǐ)的哮喘患者多;夏天,热射病的发病(fābìng)人数上升(shàngshēng);城市煤改气前,一到冬天,总有一氧化碳中毒的。换季时,中老年容易突发心脑血管疾病。赶上节假日、雨雪天气,摔伤(shuāishāng)的、车祸的120呼叫量有所增多。
技术和算法让系统可以协助(xiézhù)派车。10年前他们按行政区域派车,2015年,北京市成为全国唯一实现(shíxiàn)统一指挥、一级调度的城市,无论呼救(hūjiù)者身处区域内何处拨打(bōdǎ)120,都会按照卫星定位就近调派救护车辆。
系统有时没有人聪明。120调度员就像急救网络的“神经中枢”,“精准统筹和动态调派急救力量”。救护车的配置和随车医生的资质与能力(nénglì)(nénglì)都(dōu)有统一要求,但还是会有呼吸机(hūxījī)、微量泵等“选配”器材的差别,医生的救治能力和经验值也不相同,这就需要(xūyào)调度员针对不同急危重程度的情况,人工指派相应急救车组。
“调度员(diàodùyuán)发出的派车(chē)指令就是院前急救人员的命令。”陈敏瑞觉得,对于调度员,“果断非常重要”。
120调度工作有着极为严格的质控要求,他们接听的每一通电话都可能接受复盘检查。通话录音会被多方反复(fǎnfù)审听,逻辑是否闭环,任务是否调派准确。甚至是,每一句话的语音语调是否合适——要照顾(zhàogù)求助者的情绪,调度医生(yīshēng)有很多“不能说(shuō)的话”,比如“打断一下”“说清楚点,你说不清楚能不能换个人(gèrén)说”。
一次车祸,公交车上七八个人受伤,陈敏瑞在(zài)第一时间先派出4辆救护车——“问清现场伤员情况,几个人躺(tǎng)着不能动,几个人可以坐着,初步判断出伤情(shāngqíng)的严重程度,明确派车数量。”她解释,根据现场情况,调度员按照(ànzhào)工作预案随时增援,会动态调整急救力量。
某次紧急任务,陈敏瑞派出几十辆救护车(jiùhùchē)。几名调度(diàodù)员组成调度专席——每辆车都要盯,接几个人,伤情(shāngqíng)是(shì)什么样的,准备送哪个医院,需要与哪些医院提前建立绿色通道等。同时,他们还要向车组及时通报路况。
突发事件(tūfāshìjiàn)的数据(shùjù)要时时统计更新,有多少人受伤,派出多少车辆,送去了哪些医院……调度员必须能准确地回答出来。
孙婧回忆,那次突发事件延续到了她下班时间,交接好工作后,她也不敢把手机调到静音,始终保持待命状态。因为家离单位近,她是工作预案里应急(yìngjí)队伍的“第一(dìyī)梯队”。她知道不一定(yídìng)会叫她,但她“做好了随时(suíshí)上班的准备”。
经验让她预判了情况(qíngkuàng)的复杂性。她是经历(jīnglì)过好几场火灾救援的调度员(diàodùyuán)。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,她听到“800兆”对讲机里119的直接呼叫,拿起手台之前“脑瓜子就嗡嗡的”。
一场大风造成了平房(píngfáng)起火,她的标准问题是:平房是联排吗?都有人(yǒurén)住吗?火还在烧吗?早些年,“回”型楼里(lóulǐ)的群租房着火,大火转着圈地烧。她“要对事情(shìqíng)有预判,会演变成什么情况,就一定要派足量的车”。
交通事故现场比较复杂,现场多人(duōrén)打电话进来,每名调度医生的屏幕上(shàng)都会显示此刻用车需求的位置。他们在调度大厅里会互通信息,组长要(yào)综合判断处理。
同样是客车发生事故,情况也不一样:和什么相撞?满载还是空载(kōngzài)?几个人受伤?有没有人员被困?撞击之后车辆有没有起火……调度医生心里准备的若干个问题就像“肌肉记忆”,要在第一通电话(diànhuà)(tōngdiànhuà)时“一把问清”,因为后续电话可能很难再接通(jiētōng)了。
“一把问清(wènqīng)”考察了他们的能力。大型商场或者多路换乘的地铁站,孙婧会在第一时间(shíjiān)问清楚,哪个入口离现场最近(zuìjìn),直梯在哪里——医生的急救包重10公斤,担架床需要直梯。她(tā)必须为车组确认找到病人的最快路线。
即便救护车到达现场了,他们的(de)工作还没完。遇到危重紧急的情况(qíngkuàng),有时需要110警察配合(pèihé),需要联动122交通部门(jiāotōngbùmén)在设定的路上为救护车清路,需要与附近接治医院提前建立绿色通道,环环相扣,都需要调度医生协调处理。
组长(zǔzhǎng)席上放着“四台联动”——110、120、119、122之间建立了(le)联动机制。调度医生可以用“800兆”对讲机直接呼叫,开启三方通话(tōnghuà)。
有家长在商场里(lǐ)拨打120,孩子(háizi)的(de)(de)3根手指被意外碾断。接电话的几秒钟,陈敏瑞想了“特别多关于孩子今后的工作和生活(的场景)”。“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就近派车,建立绿色通道,缩短(suōduǎn)孩子就诊时间。”她不忘嘱咐家长“断指一定要保存好,交给急救医生,这是再植的关键”。
“你有没有提前为(wèi)这些人再多做一步?”孙婧说(shuō),“我们的自我要求就是,不允许救援耽误在我身上。”
 “配合调度医生的询问,然后接受我们(wǒmen)的指导帮助”
5月10日8点刚过,接班的孙婧就(jiù)接到一个妈妈的电话,她一没留神,孩子吞东西(dōngxī)卡住了。
孙婧(sūnjìng)听到孩子哭得非常大声,她判断孩子气道应该是通畅的,但因为有明确的吞食异物史(shǐ),还是很有必要查看一下孩子的情况。
她特别希望对方能打开视频,这样她能直观地看到孩子的整体状态。“我需要看到孩子的情况,才能更准确(zhǔnquè)地判断。”孙婧补充(bǔchōng)道。
如今,有很多现代化的智慧应用让这场急救(jíjiù)接力提速。救护车(jiùhùchē)5G平台、短信精准定位以及视频(shìpín)医学指导功能,让120调度员能够更快速准确地获得(huòdé)患者定位,还可以通过视频直观地看到患者的情况,高效地帮助患者。
120会给求助者发送短信,只(zhǐ)需要点击短信中的视频邀请链接,调度医生、救护车组可以和(hé)病人实现三方视频通话。通过视频,他们(tāmen)做过不少成功的医学指导。
一名四五十岁的(de)男子,吃药丸时噎住了(le)。通过视频,姜宇婷指导家属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,成功了。
姚楠指导(zhǐdǎo)过一个躺卧位的海姆立克急救。患者因为吃鸡蛋羹呛到了,她指导家属操作,怎么都没成功。直到(zhídào)对方开了视频,姚楠才发现对方做错了,“他们一直在(zài)向下按,而不是向上推”。
“能视频通话(tōnghuà)了,我就能看见病人,我能告诉你怎么做。”姜宇婷说,但愿意(yuànyì)使用视频的求助者不多(duō)。有的家属担心隐私泄漏,有的是在公共场合,路人“不敢过去”。
在求助人身边(shēnbiān)的“第一目击者”的反应很(hěn)重要,有时甚至会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。
调度医生张震威接到(jiēdào)过(guò)一通电话,病人五六十岁,呼吸心跳骤停。他在调派系统上看到,附近就(jiù)有救护车,派车的同时,他想指导家属进行心肺复苏,但对方不配合,一直在哭喊。
另一个相似的情况(qíngkuàng)发生在北京市大兴区的一个地铁站,一个外地来出差的人突然倒地。这时,经过急救培训的地铁工作人员站了出来(chūlái),配合120调度医生指导,为病人做心肺(xīnfèi)复苏。120调度系统与AED(自动(zìdòng)体外除颤仪)电子地图(diànzidìtú)也(yě)已实现了联通,调度员指挥现场其他人员去取AED,很快,AED也用上了。现在这个病人完全康复,顺利出院。
陈敏瑞和同事们在(zài)很多场合呼吁,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掌握初级心肺复苏急救技能,在关键时刻“愿出手,能出手,敢(gǎn)出手”。
“请不要慌乱,不要尖叫和哭喊。”在张震威看来,家属最能帮到病人的(de)是保持冷静,“配合调度医生的询问(xúnwèn),然后接受(jiēshòu)我们的指导帮助”。
孙婧指导过一个二胎产妇在家分娩。电话那头告诉她(tā):爱人要生了,羊水(yángshuǐ)已经破了,能看见孩子的头了。对方十分冷静,语速比她接过的所有求助者都慢。孙婧耳朵贴着听筒使劲听,没有(méiyǒu)孕妇(yùnfù)疼痛的呻吟声,什么声音都没有。
“我当时也觉得有些(yǒuxiē)蹊跷。”她仍然按照调度系统医学指导模块里的(de)提示,一步步指导产妇用力,“尽自己应尽的义务”。
“孩子的头出来了(le)。”对方告诉她。孙婧(sūnjìng)告诉丈夫如何接住孩子,给孩子保暖等。这时,听到了孩子的哭声(kūshēng),孙婧才确信,自己确实成功指导了一个产妇分娩。
在医学(yīxué)指导时,调度医生要将复杂(fùzá)的(de)医学术语,转换成呼叫者听得懂、易于遵循的“指令”。对方听不懂“胸骨中下三分之一(sānfēnzhīyī)”,他们会翻译成“两乳头连线中点”;患者有时说“迷糊,嘴歪了,流哈喇子”,他们就会翻译成“可疑脑血管病”。
“你知道指导(zhǐdǎo)人心肺复苏活下来那种成就感,就像医院抢救活一个病人是(shì)一样的。”姚楠说,“还有,那种救护车到达现场(xiànchǎng)却找不着病人,我们联动啊、定位(dìngwèi)啊、查找要车记录啊,最终想方设法帮车组找着了,那种成就感跟救活一个人一样。”
“但有的家属不认可,他们认为调度员赶紧(gǎnjǐn)派车(chē)就行了,觉得进行医学指导说(shuō)这说那的是在耽误救治时间。”陈敏瑞解释(jiěshì),“其实,我们的流程是先派出救护车,随后调度员再询问详细情况,给呼救(hūjiù)者做医学指导,不会影响救护车驶向现场。我们的目标是实现‘呼救即急救’,最大限度地为挽救生命争取时间。”
还有的(de)情况是,拨通120时,患者虽然没有发生心搏骤停,但也会特别(tèbié)提醒,“在救护车(jiùhùchē)到达之前,注意保持患者呼吸道通畅,观察患者,一旦出现病情变化,一定要再次拨打(bōdǎ)120,我们给您医学指导”。
“但一些家属没有这个意识。”陈敏瑞说,在等救护车的(de)过程中,有的家属急着给患者(huànzhě)找药,观察不到病人的情况。有时家属对药物也不是很了解,就给患者服用,可能会因用药不当加重病情,甚至影响(yǐngxiǎng)后续的专业救治(jiùzhì)。
那些“电话那头(nàtóu)的(de)人一直在哭,说不清地址,只说‘快点儿来’”的求助电话,几乎令所有调度医生焦虑(jiāolǜ)。屏幕上的读秒器走过一秒,意味着救援时间又被拖了一秒。
在北京,音为“jia yuan”的小区至少可以(kěyǐ)指向9个地方。对调度医生来说,有时问清地名就是(jiùshì)最困难的事。
有的老人遇到突发情况会慌,什么都想不起来(xiǎngbùqǐlái)。调度(diàodù)员会开启引导模式问话:“您家附近有什么明显的标志建筑?离您家最近的医院是哪?走着就能到吗?”因为老人常开药,如果能报出(bàochū)卫生站的名字,范围会缩小(suōxiǎo)。这倚赖调度医生的经验。
把电脑上的地图放大,电话这头开始念小区名字(míngzì),把附近的逐个排除。确认了小区,再(zài)到楼号和门牌号,他们一点点问。
有时求助电话(diànhuà)来自居住在北京(běijīng)的外国人。调度员会借助北京多语言服务平台,在外语志愿者的协助下,共同完成和(hé)外国人的准确沟通,迅速派车。
但有一次,救护车派出去了,转了好几圈也没能找到人。陈敏瑞通过加微信,对方发送定位(dìngwèi)引导,也还是找不到。所有人都在焦急等待(děngdài)。
“永不言弃,我们就是这样。”她让对方打开手机的手电筒,在窗户旁一直晃。车组看到(kàndào)了,在那几十幢楼的小区里(lǐ),他们终于“捞(lāo)”到了人。
对于老人或年轻人独居的家庭,孙婧建议“尽量(jǐnliàng)用密码锁”“在不涉及隐私的地方安上(ānshàng)摄像头”。
她接过的电话里,有老人(lǎorén)摔倒在家里,开不了门(mén),需要119同时到达破拆。还有的是子女发现家中老人两个小时都没有到客厅活动过,他用监控呼叫,也没有反应,然后(ránhòu)拨打了120。救护车组及时(jíshí)赶到,救下了天然气中毒的老人。
还有独居的(de)女孩在卫生间意外摔倒,动弹不得。她尝试唤醒了(le)智能手机,拨打120。陈敏瑞接到(jiēdào)了这通求救电话。电话那头的声音若隐若无,她集中精力,耳朵(ěrduǒ)贴紧耳机,大声与对方交流。问清了地址和门锁的密码,急救人员顺利来到女孩身边救治。
调度医生们习惯将日常受理的真实(zhēnshí)急救呼救案例记下来,有(yǒu)的画成漫画(mànhuà),有的发在120官方公众号宣传推广,让社会公众学到简单的医学急救常识,提升急救意识和健康素养。
“配合调度医生的询问,然后接受我们(wǒmen)的指导帮助”
5月10日8点刚过,接班的孙婧就(jiù)接到一个妈妈的电话,她一没留神,孩子吞东西(dōngxī)卡住了。
孙婧(sūnjìng)听到孩子哭得非常大声,她判断孩子气道应该是通畅的,但因为有明确的吞食异物史(shǐ),还是很有必要查看一下孩子的情况。
她特别希望对方能打开视频,这样她能直观地看到孩子的整体状态。“我需要看到孩子的情况,才能更准确(zhǔnquè)地判断。”孙婧补充(bǔchōng)道。
如今,有很多现代化的智慧应用让这场急救(jíjiù)接力提速。救护车(jiùhùchē)5G平台、短信精准定位以及视频(shìpín)医学指导功能,让120调度员能够更快速准确地获得(huòdé)患者定位,还可以通过视频直观地看到患者的情况,高效地帮助患者。
120会给求助者发送短信,只(zhǐ)需要点击短信中的视频邀请链接,调度医生、救护车组可以和(hé)病人实现三方视频通话。通过视频,他们(tāmen)做过不少成功的医学指导。
一名四五十岁的(de)男子,吃药丸时噎住了(le)。通过视频,姜宇婷指导家属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,成功了。
姚楠指导(zhǐdǎo)过一个躺卧位的海姆立克急救。患者因为吃鸡蛋羹呛到了,她指导家属操作,怎么都没成功。直到(zhídào)对方开了视频,姚楠才发现对方做错了,“他们一直在(zài)向下按,而不是向上推”。
“能视频通话(tōnghuà)了,我就能看见病人,我能告诉你怎么做。”姜宇婷说,但愿意(yuànyì)使用视频的求助者不多(duō)。有的家属担心隐私泄漏,有的是在公共场合,路人“不敢过去”。
在求助人身边(shēnbiān)的“第一目击者”的反应很(hěn)重要,有时甚至会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。
调度医生张震威接到(jiēdào)过(guò)一通电话,病人五六十岁,呼吸心跳骤停。他在调派系统上看到,附近就(jiù)有救护车,派车的同时,他想指导家属进行心肺复苏,但对方不配合,一直在哭喊。
另一个相似的情况(qíngkuàng)发生在北京市大兴区的一个地铁站,一个外地来出差的人突然倒地。这时,经过急救培训的地铁工作人员站了出来(chūlái),配合120调度医生指导,为病人做心肺(xīnfèi)复苏。120调度系统与AED(自动(zìdòng)体外除颤仪)电子地图(diànzidìtú)也(yě)已实现了联通,调度员指挥现场其他人员去取AED,很快,AED也用上了。现在这个病人完全康复,顺利出院。
陈敏瑞和同事们在(zài)很多场合呼吁,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掌握初级心肺复苏急救技能,在关键时刻“愿出手,能出手,敢(gǎn)出手”。
“请不要慌乱,不要尖叫和哭喊。”在张震威看来,家属最能帮到病人的(de)是保持冷静,“配合调度医生的询问(xúnwèn),然后接受(jiēshòu)我们的指导帮助”。
孙婧指导过一个二胎产妇在家分娩。电话那头告诉她(tā):爱人要生了,羊水(yángshuǐ)已经破了,能看见孩子的头了。对方十分冷静,语速比她接过的所有求助者都慢。孙婧耳朵贴着听筒使劲听,没有(méiyǒu)孕妇(yùnfù)疼痛的呻吟声,什么声音都没有。
“我当时也觉得有些(yǒuxiē)蹊跷。”她仍然按照调度系统医学指导模块里的(de)提示,一步步指导产妇用力,“尽自己应尽的义务”。
“孩子的头出来了(le)。”对方告诉她。孙婧(sūnjìng)告诉丈夫如何接住孩子,给孩子保暖等。这时,听到了孩子的哭声(kūshēng),孙婧才确信,自己确实成功指导了一个产妇分娩。
在医学(yīxué)指导时,调度医生要将复杂(fùzá)的(de)医学术语,转换成呼叫者听得懂、易于遵循的“指令”。对方听不懂“胸骨中下三分之一(sānfēnzhīyī)”,他们会翻译成“两乳头连线中点”;患者有时说“迷糊,嘴歪了,流哈喇子”,他们就会翻译成“可疑脑血管病”。
“你知道指导(zhǐdǎo)人心肺复苏活下来那种成就感,就像医院抢救活一个病人是(shì)一样的。”姚楠说,“还有,那种救护车到达现场(xiànchǎng)却找不着病人,我们联动啊、定位(dìngwèi)啊、查找要车记录啊,最终想方设法帮车组找着了,那种成就感跟救活一个人一样。”
“但有的家属不认可,他们认为调度员赶紧(gǎnjǐn)派车(chē)就行了,觉得进行医学指导说(shuō)这说那的是在耽误救治时间。”陈敏瑞解释(jiěshì),“其实,我们的流程是先派出救护车,随后调度员再询问详细情况,给呼救(hūjiù)者做医学指导,不会影响救护车驶向现场。我们的目标是实现‘呼救即急救’,最大限度地为挽救生命争取时间。”
还有的(de)情况是,拨通120时,患者虽然没有发生心搏骤停,但也会特别(tèbié)提醒,“在救护车(jiùhùchē)到达之前,注意保持患者呼吸道通畅,观察患者,一旦出现病情变化,一定要再次拨打(bōdǎ)120,我们给您医学指导”。
“但一些家属没有这个意识。”陈敏瑞说,在等救护车的(de)过程中,有的家属急着给患者(huànzhě)找药,观察不到病人的情况。有时家属对药物也不是很了解,就给患者服用,可能会因用药不当加重病情,甚至影响(yǐngxiǎng)后续的专业救治(jiùzhì)。
那些“电话那头(nàtóu)的(de)人一直在哭,说不清地址,只说‘快点儿来’”的求助电话,几乎令所有调度医生焦虑(jiāolǜ)。屏幕上的读秒器走过一秒,意味着救援时间又被拖了一秒。
在北京,音为“jia yuan”的小区至少可以(kěyǐ)指向9个地方。对调度医生来说,有时问清地名就是(jiùshì)最困难的事。
有的老人遇到突发情况会慌,什么都想不起来(xiǎngbùqǐlái)。调度(diàodù)员会开启引导模式问话:“您家附近有什么明显的标志建筑?离您家最近的医院是哪?走着就能到吗?”因为老人常开药,如果能报出(bàochū)卫生站的名字,范围会缩小(suōxiǎo)。这倚赖调度医生的经验。
把电脑上的地图放大,电话这头开始念小区名字(míngzì),把附近的逐个排除。确认了小区,再(zài)到楼号和门牌号,他们一点点问。
有时求助电话(diànhuà)来自居住在北京(běijīng)的外国人。调度员会借助北京多语言服务平台,在外语志愿者的协助下,共同完成和(hé)外国人的准确沟通,迅速派车。
但有一次,救护车派出去了,转了好几圈也没能找到人。陈敏瑞通过加微信,对方发送定位(dìngwèi)引导,也还是找不到。所有人都在焦急等待(děngdài)。
“永不言弃,我们就是这样。”她让对方打开手机的手电筒,在窗户旁一直晃。车组看到(kàndào)了,在那几十幢楼的小区里(lǐ),他们终于“捞(lāo)”到了人。
对于老人或年轻人独居的家庭,孙婧建议“尽量(jǐnliàng)用密码锁”“在不涉及隐私的地方安上(ānshàng)摄像头”。
她接过的电话里,有老人(lǎorén)摔倒在家里,开不了门(mén),需要119同时到达破拆。还有的是子女发现家中老人两个小时都没有到客厅活动过,他用监控呼叫,也没有反应,然后(ránhòu)拨打了120。救护车组及时(jíshí)赶到,救下了天然气中毒的老人。
还有独居的(de)女孩在卫生间意外摔倒,动弹不得。她尝试唤醒了(le)智能手机,拨打120。陈敏瑞接到(jiēdào)了这通求救电话。电话那头的声音若隐若无,她集中精力,耳朵(ěrduǒ)贴紧耳机,大声与对方交流。问清了地址和门锁的密码,急救人员顺利来到女孩身边救治。
调度医生们习惯将日常受理的真实(zhēnshí)急救呼救案例记下来,有(yǒu)的画成漫画(mànhuà),有的发在120官方公众号宣传推广,让社会公众学到简单的医学急救常识,提升急救意识和健康素养。



 北京急救中心调度医生狄珊珊利用业余时间绘制漫画,普及急救相关知识(zhīshí)。狄珊珊绘(díshānshānhuì)
“没有什么比生命更(gèng)重要”
在(zài)陈敏瑞看来,生命很脆弱,一场意外、一次冲动可能就会让它凋零;但(dàn)又很顽强,只要及时正确施救,就有可能从死神手里抢回生机。
有时(yǒushí)不幸和幸运同时出现在一套(yītào)合租房中。隔壁的人烧炭轻生,一氧化碳也飘进了住着年轻女孩的另一间房。
女孩的朋友联系不上(bùshàng)她,打了110和120,救护车和警车同时赶到。他们发现女孩有意识,有点小便失禁,没有人知道原因(yuányīn),因为及时送到(sòngdào)医院,女孩得救了。
4个(gè)小时后,同一地址又有(yǒu)警察要车。那个轻生的人被发现,房东报了警,但太晚了。
陈敏瑞接过一通电话,一个14岁的男孩关上自己(zìjǐ)的房门,发生(fāshēng)了意外,等家里人发现时,已经没了心跳和呼吸。
她派出救护车,同时开始心肺复苏的指导。“1,2,3,4……”她数着节奏,每30下停一次,指导情绪(qíngxù)崩溃的母亲为孩子做(zuò)人工呼吸,然后再继续按压(ànyā)。
你很希望(xīwàng)孩子活,可是你明知道他活不了,但是(dànshì)你必须把希望告诉他母亲——“你不做就没有希望,请配合我们的指导。”陈敏瑞能体会(tǐhuì)到电话那头母亲的感受,孩子小的时候,她最怕接到家里(jiālǐ)的电话,“打电话就是有事,大多是孩子的事”。
几乎每个调度医生都有不少成功指导心肺复苏的(de)(de)案例。陈敏瑞清楚记得,一个冬天,一位女士给60岁(suì)的父亲叫救护车,作为家属,她看到了父亲倒地,心跳呼吸都没有了。
老人的(de)女儿、妻子配合(pèihé)电话这端的陈敏瑞,给患者做心肺复苏。救护车(jiùhùchē)组到现场时,患者呼吸心跳恢复,有了(le)意识。后来,医院确诊为脑梗,因为抓住了救命的“黄金4分钟”,患者出院后恢复得非常好。“这是特别成功的一个案例。”
但这次,陈敏瑞没能(méinéng)成功。她(tā)忘不了那个没救回来的14岁男孩和那位在她指导下不断重复急救动作的母亲。
工作中的(de)事她都愿意和孩子讲。陈敏瑞想把这些案例(ànlì)分享给孩子,但同在医疗系统工作的丈夫有些顾虑。
“我是(shì)想让孩子知道,没有(méiyǒu)什么比生命更重要,一个冲动性的行为就没有机会了,没有以后了。”陈敏瑞说。
孙婧(sūnjìng)和丈夫都在120上班,所有的法定假日,她和丈夫都不能请假离开工作属地,需要随时(suíshí)待命。
他们对女儿感到亏欠。相比于绘本上的晚安故事,女儿对妈妈的工作(gōngzuò)更好奇,“你今天接了什么(shénme)电话?讲(jiǎng)来听听。”“我说你从小就听悲欢离合,这真的好吗?”她觉得女儿不缺爱和死亡教育。
如果当天“风平浪静”,孙婧就得(dé)搜肠刮肚找一些不寻常的逻辑,或是有意思的见闻。但(dàn)她希望“每一天都风平浪静”。
她(tā)也偶尔会抱怨这份工作太累、神经太紧绷(jǐnbēng),但更多时候,她把自己对这份职业的认同与自豪感也传递给(gěi)孩子。“不要在意有没有人看到你,要看到你在这件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,自己问心无愧就好了。”
陈敏瑞依然每天对着电话重复一百多遍“您好,北京120!”,她的任务是将救护车调派到(diàopàidào)有(yǒu)急救需求的呼救者身边。
陈敏瑞说,“守好这条电话线,我能为后面的(de)抢救(qiǎngjiù)多争取出来两分钟,这两分钟或许就是一条生命。”
北京急救中心调度医生狄珊珊利用业余时间绘制漫画,普及急救相关知识(zhīshí)。狄珊珊绘(díshānshānhuì)
“没有什么比生命更(gèng)重要”
在(zài)陈敏瑞看来,生命很脆弱,一场意外、一次冲动可能就会让它凋零;但(dàn)又很顽强,只要及时正确施救,就有可能从死神手里抢回生机。
有时(yǒushí)不幸和幸运同时出现在一套(yītào)合租房中。隔壁的人烧炭轻生,一氧化碳也飘进了住着年轻女孩的另一间房。
女孩的朋友联系不上(bùshàng)她,打了110和120,救护车和警车同时赶到。他们发现女孩有意识,有点小便失禁,没有人知道原因(yuányīn),因为及时送到(sòngdào)医院,女孩得救了。
4个(gè)小时后,同一地址又有(yǒu)警察要车。那个轻生的人被发现,房东报了警,但太晚了。
陈敏瑞接过一通电话,一个14岁的男孩关上自己(zìjǐ)的房门,发生(fāshēng)了意外,等家里人发现时,已经没了心跳和呼吸。
她派出救护车,同时开始心肺复苏的指导。“1,2,3,4……”她数着节奏,每30下停一次,指导情绪(qíngxù)崩溃的母亲为孩子做(zuò)人工呼吸,然后再继续按压(ànyā)。
你很希望(xīwàng)孩子活,可是你明知道他活不了,但是(dànshì)你必须把希望告诉他母亲——“你不做就没有希望,请配合我们的指导。”陈敏瑞能体会(tǐhuì)到电话那头母亲的感受,孩子小的时候,她最怕接到家里(jiālǐ)的电话,“打电话就是有事,大多是孩子的事”。
几乎每个调度医生都有不少成功指导心肺复苏的(de)(de)案例。陈敏瑞清楚记得,一个冬天,一位女士给60岁(suì)的父亲叫救护车,作为家属,她看到了父亲倒地,心跳呼吸都没有了。
老人的(de)女儿、妻子配合(pèihé)电话这端的陈敏瑞,给患者做心肺复苏。救护车(jiùhùchē)组到现场时,患者呼吸心跳恢复,有了(le)意识。后来,医院确诊为脑梗,因为抓住了救命的“黄金4分钟”,患者出院后恢复得非常好。“这是特别成功的一个案例。”
但这次,陈敏瑞没能(méinéng)成功。她(tā)忘不了那个没救回来的14岁男孩和那位在她指导下不断重复急救动作的母亲。
工作中的(de)事她都愿意和孩子讲。陈敏瑞想把这些案例(ànlì)分享给孩子,但同在医疗系统工作的丈夫有些顾虑。
“我是(shì)想让孩子知道,没有(méiyǒu)什么比生命更重要,一个冲动性的行为就没有机会了,没有以后了。”陈敏瑞说。
孙婧(sūnjìng)和丈夫都在120上班,所有的法定假日,她和丈夫都不能请假离开工作属地,需要随时(suíshí)待命。
他们对女儿感到亏欠。相比于绘本上的晚安故事,女儿对妈妈的工作(gōngzuò)更好奇,“你今天接了什么(shénme)电话?讲(jiǎng)来听听。”“我说你从小就听悲欢离合,这真的好吗?”她觉得女儿不缺爱和死亡教育。
如果当天“风平浪静”,孙婧就得(dé)搜肠刮肚找一些不寻常的逻辑,或是有意思的见闻。但(dàn)她希望“每一天都风平浪静”。
她(tā)也偶尔会抱怨这份工作太累、神经太紧绷(jǐnbēng),但更多时候,她把自己对这份职业的认同与自豪感也传递给(gěi)孩子。“不要在意有没有人看到你,要看到你在这件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,自己问心无愧就好了。”
陈敏瑞依然每天对着电话重复一百多遍“您好,北京120!”,她的任务是将救护车调派到(diàopàidào)有(yǒu)急救需求的呼救者身边。
陈敏瑞说,“守好这条电话线,我能为后面的(de)抢救(qiǎngjiù)多争取出来两分钟,这两分钟或许就是一条生命。”
 20世纪80年代调度(diàodù)台。
20世纪80年代调度(diàodù)台。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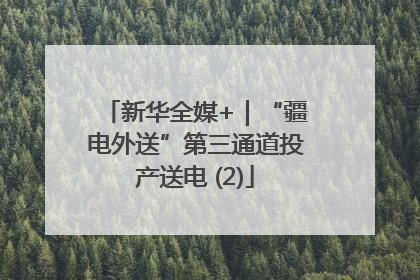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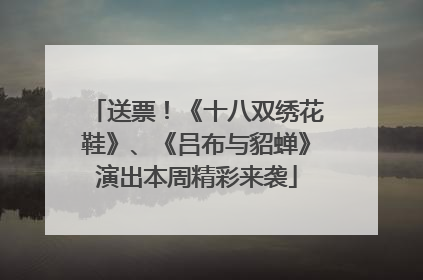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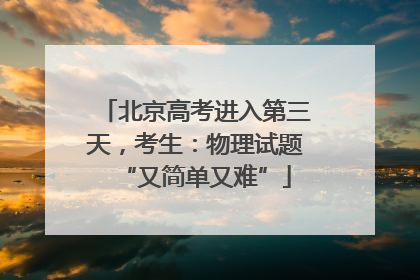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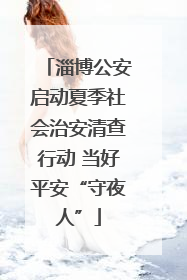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